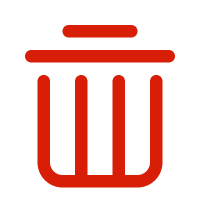建構自己的座標系:從原點O開始
2025/5/16
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系友 林妍羽

失真的航道
悠閒的午後,電視節目往往是學生時期最單純的娛樂與救贖。
還記得小學時,我喜歡收看〈快樂有go正〉這個電視節目,其中,「事實勝於雄辯」和「沉默是金、雄辯是銀」是節目的經典台詞。身為小學生的我,對於出現的提問、選項、判定,以及最後的答案揭曉,除了感受到猜測時的緊張、答對時的快感及誤判時的疑惑,也開始隱約發覺自己對於法律的喜好。
「我要進入司法體系。」
於是,在9歲那年,在人生無邊無際的這片汪洋中,我從此有了精準前進的座標與方向。
這個夢想,也讓我在國三大考前的祈願與眾不同。有別於他人落筆寫下「考上第一志願」,我反而是在那希望樹上繫上「順利就讀法律系」的心願。進入高中的我,理所當然地參加了辯論社,憑藉對法律的熱情,我當上社長、拿了最佳辯士,同時更不斷參加與法律相關的競賽及測驗,努力累積相關的經驗,只願未來面試時能去觸碰我的夢。
然而,在體制中的思辨路徑下,我卻遺忘了人性——人性被挑戰了兩千年,始終如一。
高三前夕,我們迎來了最後一場辯論比賽,原以為只是一場例行賽事,卻臨時增設了「最佳辯士」的評選,這是當時候未被事前說明的競爭。猝不及防的出現,讓原先與我無話不談的社員,為爭奪頭銜而鬩牆。那份年少的憧憬,最終囿於公設辯護人的訴諸,致使我原以為法律張揚的正義,是為被棄絕者發聲,沒想到卻得顛倒是非、扭曲真意。
於是,高三那年,我放棄了近十年的夢想,自此,我在人海漂流,沒有盡頭。
巨浪分流,無頭緒的憂愁
當我決心放棄法律系的時候,距離大考約莫剩下200天,這是個瘋狂且大膽的決定,當下的我甚至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承擔這個選擇背後的責任。我只知道,自己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,如果此生得違心生存,那不叫活著,生命不該以這個方式延續。
基於某種無法言喻的窘迫,我不敢和父母、老師及朋友說,只能埋頭苦讀,高三考生的身分能再幫我掩蔽一陣子。但該來的終究會來,因著人際關係的裂痕、對前途的迷茫,我的學測成績幾乎是當初模擬考的八成,大考失常,眾人驚嘆,紛紛追問緣由,我才終於說出口,但那時的我仍舊茫然,沒有方向,更沒有答案。
隨著推甄與繁星陸續結束,班上仍在為指考(現在的分科測驗)努力的人只剩下我。放長假的第一天中午,我極度不適應空蕩的午間時光,原先眾人一同小憩的時光,如今只剩我一個人掙扎。就在這時,午餐阿姨打電話告知:「因為班上學生只有你一個人,所以班上的飯菜得自己去合作社盛或是購買。」我一個人正在思忖著午餐該如何解決,卻看見班導師自走廊另一端匆匆趕來,急切地對我說:「好險你還沒去盛飯,我已經買好我們的午餐了。」他停了停,接著說:「以後就到教師辦公室,我陪你一起吃,這條路很辛苦,但老師會陪著你。」
與社員吵架時,我沒有哭;放棄法律夢時,我沒有哭;大考失常,我也沒有哭。但那個午後,因著這句話,我在教師辦公室嚎啕大哭,把無以名狀的恐懼、迷惘、徬徨和壓力一股作氣地宣洩而出,在我底心彷彿聽到一股聲音,如果生命要延續,我希望可以傳遞這份溫暖和感動。
那個午後,我告訴自己,也許我可以考慮與教育相關的領域。
回首莫忘來時路,再盼已成亙古道
指考落幕,我踏入了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。在我上了一個學期的課程後,我向自己提出了疑問:「要如何成為一名好老師?」、「我要如何在學校,一待就是四十年,過著日復一日的生活?」這些問題困擾著我,也成為我遲遲無法下定決心「成為一名老師」的原因。滴水之恩,當湧泉相報,但我卻猶豫著,擔心自己無法回應當初那份感動。
於是我決定去請教專家,已身居高位的教授,我想知道以他的視野,如何看待這年輕靈魂的飄泊。「當你會這麼問的時候,不就代表你其實已經算是一位好老師了嗎?」「我也當過教師,但一所學校不應該只有教師,學校所需要的人才太多,在教育上更是有許多不同的方向,不妨就看看自己能到哪裡去吧!每一個位置的體驗,都會提供給你不同的思考。」
教授的三言兩語,撫平了我的波瀾。若我的高中老師給了我感動和溫暖,那麼,我的大學教授給我的則是在人生這龐大的座標系中,回到原點O(0,0)的可能,讓我不再迷惘,為生命的延續找出意義。
定位自己的時區,界定自己的經緯
在教育系的四年,我建構自己對於學習和教學的認知,以所學驗證體制,結合過去研讀法律的內容加以思考批判教育,並以當年參加辯論社的經驗與歷練征戰了教師甄試,也透過教育延續原初的感動與溫暖。即便我曾迷茫、驚怯跟憂慮,但因著老師們的指引,讓我在廣袤的座標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。我想生命的歡愉,正在於自己能夠賦予他人意義,唯有真實的存在,這人生才值得好好過活。
◆延伸閱讀:想進一步了解這個校系所屬的學類內容嗎?點進來看看學類介紹吧!